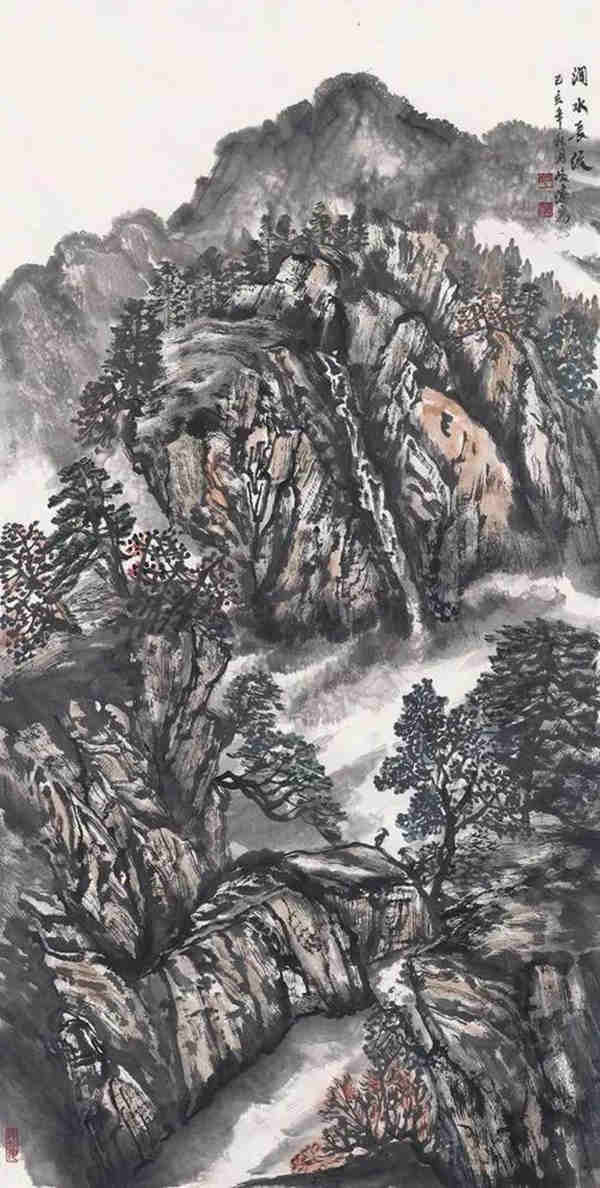
时光进入2020,屈指算来,我在陕西美协工作已10年有余了。
生命有限,人的一生没有几个10年,10年可以构成生命历程的一个单元。之所以回望这10年,是因为在这一单元,我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领域,经历了生命中无法摒弃、难以割舍的迷乱与困惑,喧哗与沉静。那种惶恐、迷茫和孤独,甚至无助和绝望,让我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尤其是我的亲身经历引发的思考、认识和体悟,都需要做理性的梳理。当然,我的梳理不会拘泥于某些事件的琐屑过程,包括这个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结。我将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谈谈这10年来有关艺术本真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我的工作单位陕西美协,这个位于西安钟楼广场西北角的地方,是在古城长安的中心,也是现代都市西安的繁华所在。这里从早到晚人流如潮,熙熙攘攘,每天可以听到从远古深处传来的晨钟暮鼓的回声,也可以听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游客的方言土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时刻,钟楼和鼓楼周边的高楼、商场、街道和店铺,霓虹闪烁,流光溢彩,梦幻一般妖娆,令人流连忘返。
当我第一次靠近那个灰色铁皮大门,看到铁门两侧巍然耸立的高楼和高楼下的小院,小院两旁破旧低矮的简易楼房,几乎有一种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我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那是1979年我考上初中专,父亲送我上学特意绕道西安逗留一晚。第一次从山区来到西安的大街,高楼仰得我头晕目眩,看什么都新奇。晚上街上的霓虹灯闪得眼花缭乱,好像来到了人间天堂一般。当时我们住在北大街一个小旅馆里,过路时就看见街西有一个窄窄的门洞,挂了一个“美术家画廊”的牌子。从那个门洞望进去,是一个深深的通道,幽暗而神秘。我并不知道美术家画廊是什么单位,只觉得门口站的那个清瘦的头发花白的老头显得仙风道骨,气宇不凡。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当年的石鲁吧。
后来,我知道当年的美术家画廊就是今天美术家协会的所在地,门牌编号为西安市北大街32号。
当我站在这个小院里的时候,那种记忆里的幽暗和现今的破落感,很快随着新来的兴奋和激动烟消云散。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小院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在陕西美术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小院。小院虽小,但事业不小,小院虽陋,但天地宽广,这地方竟是神圣之所在。
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诞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唯一得到全国美术界认可的长安画派,走出了一批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光彩一页的响当当的人物——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国画大师,他们都堪称古城西安的另一座钟楼。
初到美协的日子,曾有老同志向我介绍,当年石鲁住什么地方,谁谁谁在哪办公,顿时感觉脚下的每块水泥地都布满他们的脚印,他们的眼睛正隐匿在某个地方盯我,一时间走路、说话都要悄声静气,生怕惊扰了他们的创作,变得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二
我在诚惶诚恐中开始了美协的工作。
这种诚惶诚恐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我对小院的敬仰,二是美术对我是一个陌生而全新的领域,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如果我说对美术还有兴趣的话,那还要追溯到我的小学。那时小学有美术课,老师教我们画一些苹果、水杯之类的简笔画。我学得很刻苦,每次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认认真真地画在道林纸作业本上,老师常常打“优”予以鼓励。画着画着,也模仿自己读的小人书,学画人物。有一次,我还为弟弟画了一幅肖像,贴在我家的窑壁,来人看了都说极像,夸我聪明好学,这更激发了我对学习美术的兴趣。这期间,我又喜欢上了毛笔字。尽管那时用麻纸临帖交作业,但常常不得要领,写得扭七裂八。后来去舅舅家,见表哥将自己的字写得工工整整贴在墙上,觉得美得不得了,也好生羡慕。后来才知他写的是汉隶,魏体。索他一张字后,我也试着模仿、练习起来。后来学校出板报,村里写阶级斗争标语,因为没几个人能写,村支书赶鸭上架,硬拉我去写了一回。支书看后大喜,以后就一直让我写,还能换得几个工分,为此父母满心欢喜。再后来上了初中,就没有美术课了,我对美术的兴趣也渐渐淡了下来,一门心思地做起了文学梦。
现在,我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一下子让我和美术离得这么近,而我那点少得可怜的美术记忆,简直不值一提。可是为了工作,我又不得不做一些准备,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说傻话、外行话,让人当白痴看呀!
本着这个最低的要求,在调动之前,我就开始准备功课,去书店买了几本美术史、美术理论之类的书啃读起来。
初到美协,我的家室还在外地,干扰较少,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啃读这些书籍。说实话,这些书并不好读,甚至显得十分枯燥,我硬着头皮读了十之七八,就有些偷懒耍滑,提不起精神。但我从此知道,美术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学科,要想学有所获,那真是高山仰止,并非一日之功。
我绝不否认,那些经过长时间专业学习、专门训练的谓之“科班出身”的人,是终有所获终有大成的人,但艺术创作往往还有个例,还有反向思维。事实证明,有许多杰出人物都不是科班出身,他们半路出道,却成一代大家,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南宋著名画家萧照曾在太行山当强盗,偶遇宫廷画师李唐便拜师求学,后入南京宫廷画院,成为魁首;《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当年奔波仕途仅为小吏,又受累入狱数载,50岁以后才正式拜师学画,80岁时终成一代名师。齐白石少年时体弱多病,家里一贫如洗 ,为了学门手艺,拜师学木工,但由于气力小,地位低,后改学小器。在学小器雕花的过程中,他一边做雕花工艺一边学美术,最终成为画坛巨匠。
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创造,个体劳动,这种创造和其他劳动都有共同点,那就是:必须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必须具有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必须热爱如初,矢志不渝;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质:
首先是对艺术要有浓厚的兴趣。兴趣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身内在生发的兴奋和趣味。生命内在生发的兴奋,与生命的成长一路前行,成为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创造之源,由此激发的创造热情和趣味感将伴随终生。
其次,具有丰厚的生活阅历。这种生活阅历包括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和学习得到的全部内容,其中的曲折、艰辛、痛苦和磨难,将形成自己的人生感悟,需要急切寻求艺术的表达之门,如熔岩一般具有极强的冲击和爆发力。
第三,要有一个比较特殊或特定的生活环境。这种特定或特殊环境从大的方面看,可以说是由时代决定的,时代发展的大势,时代所具有的创新洪流,都是激发一切艺术创造的前提。从小的方面说,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际遇是激发艺术创造的内动力,包括个人的家庭环境,周围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这些环境因素和个人的兴趣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艺术生根发芽的沃土。
第四,大凡一切有成就的艺术家都精神独立,精神孤独。精神独立是指艺术家经过长时间的艺术实践和创造形成的具有对客观世界的独立思考的看法和认识。这种看法和认识在某些方面甚至偏激,但却具有个性和魅力。精神孤独是内心排斥一切外界诱惑之后形成的心态,这种心态最明显的特征是内心的安静。只有安静下来,独立的思考才能随之前行,才能促成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但孤独不是孤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艺术创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
最后一条,勤奋、刻苦、坚持是迈向成功的阶梯。如果一个艺术家具备了上述几个特质,但自身懒惰,没有毅力和恒心,做事不能坚持到底,那就会半途而废,功废而败。
我承认天赋,但不承认天才,有些人从小就具有出类拔萃的艺术天赋和禀性。如果这种天赋和禀性能与以上的特质结合,真可谓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无数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都是经过后天学习和努力,才得以成为艺术家。因此艺术创造之路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地付出和努力,才会有所收获。那些企图以走捷径,以投机取巧为能事的人,虽能获得一时风光和几个掌声,但终不能长久。
到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我这是要选择学习绘画吗?是在为自己学习绘画找理由吗?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终于做出选择:后半生学习国画。
做出这样的决定,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可笑。
可笑的是,命运仿佛总是在捉弄我。一个因为家穷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读过中文专业的人,却偏偏喜欢文学,十几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长篇小说,创作了近百万字。虽无多大成就,但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人戏谑为“作家”了。而现在又阴差阳错,命运再次让一个没有受过美术训练,没有受到专门教育的人从事美术工作,并且还异想天开,学国画。
这不是很可笑很天真很草率吗?
人生的要害之处,在于选择。
选择是多样的,选择是一把双刃剑。
选择了一些东西,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选择了什么,就选择了什么带来的痛苦与欢乐。
世上没有一种选择不包含痛苦与欢乐。痛苦与欢乐并存,应是所有选择的全部内涵。至于其中痛苦与欢乐的占比,就要看个人的心态和心境了。
但是一旦选择了,最重要的是能否坚持这种选择。如果坚持了,并且努力地以全部的力量坚持了,就能获得这种选择和坚持所给予的某种回报,而一旦半途而废,那将一事无成。这犹如一场马拉松赛跑,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人在四十岁以后,应该说选择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因为生命留给我们的时间已很有限,用这有限的生命去做一种赌注似的选择,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这时候的选择非经深思熟虑,决不可投机和侥幸。
我是四十五岁选择美术工作的。
我非常清楚我将失去什么,也非常清楚我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这仿佛是下了一次输不起的赌注,令我惶惑而又迷茫。
但是既然选择了,那就要一条道走到底。
扪心自问,你一个没有受过美术基础训练的人,现在要学习美术能行吗?学什么,又怎么学呢?
开始真有点老虎吃天没法下爪的感觉。
但细细想来,任何东西都有规律可循。如果掌握了一般的规律,初学美术时也就不会知难而退了。
对于中国美术而言,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国画了。
中国画是几千年来扎根中国文化沃土、土生土长的民族艺术菁华,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艺术风格,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
按照艺术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按描写对象的不同划分,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各自形成的既有经验和理论总结。
但纵观中国当代的文论和画论,不管是采用哪种形式,中国画首先关注和强调的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怀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从主观上要反映出画家的意,从客观上要表现物象的神,这便是中国画的“传神论”和“写意论”。无论顾恺之的“传神论”,还是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及其六法等,讲的都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化,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物为我用”。
我认为不管是写意还是传神,基本上都存在一个技和艺的问题。
先来看看技的问题。
中国画的绘画工具,从毛笔、宣纸、墨汁、毛毡到颜料、印石,都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从人学会使用工作到创造工具,人类才得以进步发展,才有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画自从有了这些独特工具,才使得中国画的技术传承下来,不断创新发展。
中国画的笔是最重要的劳动工具,它好比我们在土地上使用的铁锨、镢头、镰刀一样,只有掌握和熟悉了这些工具的特性以后,才可以得心应手高效率地劳动。
过去我在农村用镰刀割麦子,那种长把的镰刀如果蹲下割,怎么也割不快,但若半蹲起来割,猫着腰就割得非常快,也能感到这种长把镰刀的好处了。
笔墨技法是中国画最重要的基础,历代画家都将“笔墨”作为一条重要标准。
笔和墨是绘画劳动的两个抓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就像铁锨、镢头同土地的关系一样,失去任何一个,其作用都毫无意义。
笔必须通过墨才能显现出笔的各种痕迹,而墨又必须通过笔方能产生各种墨色、墨阶效果。
熟悉笔,必须深入了解笔的毫材、笔尖、笔腰、笔根在作画过程中的作用。用笔毫不同的部位,其墨、水、色的分量不同,效果也不尽一致。笔锋行笔时,有中锋、偏锋、侧锋、卧锋等,另外还有藏锋、露锋、顺锋、逆锋等差异,若不熟练各毫各锋的作用和方法,即使能驾驶住毛笔,画面也难得有千变万化的效果。
笔以力的作用,力的大小产生轻重、缓急的变化;墨因含水多少而产生浓、淡、枯、湿的墨韵;以笔驱使墨,以墨表现笔,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因此笔所到之处,既能显示笔的功能,又能表现墨的效果。
所谓用笔,其实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笔本身,不同的笔毫与墨水、色和纸作用后,产生的效果不同;二是画者以腕、臂不同力的作用于笔端,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包含了作者的形与神、气与力。
笔主气、墨主韵。从古至今,在绘画理论之中,“气”与“韵”紧密相连,历代画家均有经典论述。五代荆浩在其《笔法记》中有“六要”的论述,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此气韵置于重要地位;北宋韩拙以诗 “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高度概括了笔墨之间的关系。可见笔墨犹一对情侣,紧紧融合在一起,把情化为力,把力注入笔端。笔的运动以线为主,以点线面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线就成为中国画写形造物和传神写意的关键。
我感到中国画的“技”,通过专业学习训练或自己勤学苦练,都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要谈到中国画的“艺”,那就非常艰难了。所谓“艺”,我认为就是画者通过描绘客观物象表达思想情感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它能使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思想受到感染和启迪。因此国画作品所传递的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也决定作品的高下与成功与否。
这就反映出,国画作品其实是对作者文化修养、思想境界、人生阅历、认识水平和思维敏锐程度等综合因素的考量,也是区分匠者和艺者的重要标尺。
当然“技”和“艺”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艺”没有“技”的承载和表现难以表达,“技”只有准确地表现“艺”,方可见其光华。二者相辅相成。
武美云供稿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