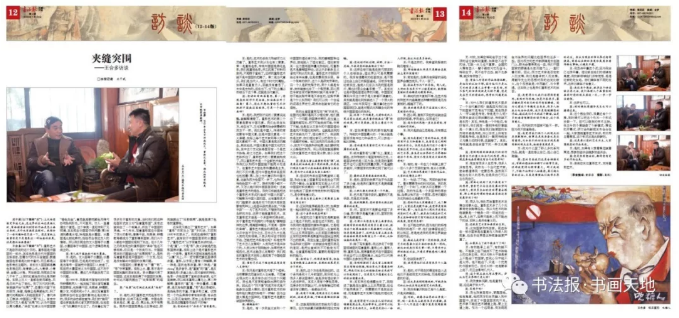

王合多(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艺术家简历:
王合多 1953年出生于河南巩义。重彩艺术家。湖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王合多 纸本重彩 吹糖人
夹缝突围——王合多访谈
书法报记者 兰干武
兰干武(以下简称“兰”):上次给您做完专版之后,在业界的反响还是挺大的,有些读者会问到您的作品是怎么画出来的,另外也有画家在探讨。我综合了一些问题和您交流一下。您在宣纸上做重彩是不是想表达一种油画的效果,还是想向油画靠拢?
王合多(以下简称“王”):重彩艺术不是您所说的这个目的。重彩画是中国画的一部分,其实色彩是古代中国画的主体语言,您看古代的永乐宫壁画、敦煌壁画色彩都是比较丰富的,而且都是以色彩表达主题的。其实古人画画都是靠色彩表达的,有青绿山水,大青绿、小青绿、金碧山水等。再如岩画,到现在已有几千年了,上面的红颜色依旧还是很鲜艳。实际上古人一直都在使用颜色,只是后来产生了变化。到了汉代的时候,审美就开始“尚黑”了,您看汉代留下来的服饰、房屋、棺椁全是黑颜色的,到了唐代尚黑就深入到绘画里面了。唐代诗人王维讲:中国画以“黑”为上。其实中国古代文人都是“尚黑”的,认为中国画以黑为最美。“诗圣”杜甫认为中国画要“惜色如金”,意思就是要把颜色用得巧妙和恰到好处,不可滥用。古人一直遵循这个道理。这个审美一直延伸到了元明清,其实现在中国画仍然把墨(黑)定调到最高水准,标准就是水墨画。水墨画是比较纯粹的,恰恰符合表达文人的情结。所以我们现在的文人画等于水墨画,水墨画等于中国画,这个逻辑思维是成立的。
兰:有人说中国画就叫做水墨画。
王:是的。文人画等于水墨画,水墨画等于中国画,已经是约定俗成了。但是这等号一画就把中国画引入歧途了。现在把水墨画定义为中国画,这不利于中国画的发展。最近几年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1995年,我做美术馆馆长的时候和钟儒乾两人一起发起了湖北省写意重彩画群体,包括聂干因、朱振庚、钟儒乾、戴少龙、郑强和我6个人,湖北写意重彩画群体当时在全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的杂志都在宣传,我们的“御用”理论家就是湖北省文联的祝斌,但他在一次飞机事故中去世了。后来鲁虹写了很多关于重彩的文章,当时我们把这种绘画形式定义为“写意重彩画”,其实这就站住了一个制高点,抓住了中国画的灵魂。十几年来,写意重彩画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影响,像聂干因、朱振庚、钟儒乾等都成为了重彩精英画家,我们六个人都在中国画坛受到了关注。但十几年之后我发现当时重彩画的“革命”性还不够彻底,仅仅是一个改良行为。中国画根本的问题就出在“尚黑弱彩”上,虽然写意重彩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分支,但还是没有解决中国画的发展问题。
中国画的三要素是“水”“墨”“彩”,“彩”非常重要。实际上水、墨、彩才是中国画完整的语言体系。若水墨就代表了中国画,这其实是阻碍了中国画的发展,针对此问题我提出了“尚彩弱黑”的理念。
兰:“尚黑”把它倒过来就是“尚彩”了。
王:是的,我们重彩艺术把色彩作为主体语言,但并不是反对墨。中国色彩体系是红、黄、蓝、白、黑五色,其中有黑色。既然中国画里黑色占主导地位,那我就提出了“尚彩弱黑”,就是强调了色彩的重要性。
近来我又提出了“重彩艺术”。如果“重彩”后面加上“画”字的话,又回到1995年的原点了。我现在倡导的“重彩艺术”,就有别于中国画里面的水墨画了。“重彩艺术”从字面意思来讲的话,一个是“重”,一个是“彩”,狭义讲就是把色彩画得浓重,实际上这个是对重彩艺术的一个误导。重彩艺术里纸本施彩法是“以薄”为上,不一定非要把颜色画得很浓重。重彩,从字面上看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画的色彩浓重;第二种是:“重chong”是多音字,是“重复”的“重”,是反复施色彩(多遍上色),因为宣纸的特性,色彩一次性画厚了宣纸容易破损,也不宜装裱,所以纸本重彩以薄为上;第三种解释:重彩的“重”是一种分量感、力量感,是沉甸甸的重量。“彩”是五彩缤纷,是指色彩的丰富,丰富多彩之意。试想把一个作品弄得非常有体积感、有杀伤力,以及沉甸甸的,再加上色彩的丰富性,您说这幅重彩作品好不好嘛?
兰:您说的这个“杀伤力”蛮有意思。
王:是的,艺术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太厉害了。重彩艺术我认为也有三要素。第一是重视色彩,传统中国画是弱化色彩,我们是重视色彩,并且拓宽了材料的使用,不局限于宣纸了,这样的重彩艺术就不是中国画的范畴了。第二是当代意识,我们是当代人,有这个时代的属性,如果只是重复古人,那就没有意思了。未来是未知的,活在当下,当下的土壤必然结当下这个果,这就是当代意识。
兰:您讲的有两层意思,第一,您现在的创作不是油画,和油画拉开了距离?第二,您也不想把重彩艺术归纳到中国画这里面来,它是一个独立画种?
王:是的,我把刚才说的三要素说完整,就解释清楚了。重彩艺术的第三个要素是要有中国元素。我们生活在东方,活在当下,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都和西方不一样。我们是中国人,传承的肯定要有中国元素,但是中国元素是一个大课题,实际上每个艺术家所导入的中国元素都不一样。中国元素是宽泛的概念,具体地说,中国元素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其中这个文化脉络里面有一个是艺术脉络,称之为艺脉。如果我们把这个艺脉抓住了,重彩艺术的三要素就构成了,所以重彩艺术是一个全新艺术体系,和我们认知的中国画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在重彩艺术里色彩和墨都是主角。我们不反对墨,因为中国色彩体系里面也包括墨(黑),加上当代意识和中国元素,这就和西方绘画不一样了,也和中国传统绘画不一样了。既然和哪个都不一样,又怎么能归到中国画里面呢?这就是重彩艺术的理念。我的目标就是把这个重彩艺术形式打造成“中国人的画”,可解释为中国人画的画。还有重彩艺术的门槛要求:就是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里要有两种以上绘画手段的混合体,“不择手段”——为了艺术目的,不惜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样才能搞重彩艺术。其实重彩艺术就是一个多画种的混合体。关于重彩艺术我提的口号就是“模糊画种的边界,混淆画种概念,不受某一画种的束缚”。重彩艺术提法的诱因是:人类认识宇宙才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是人类的无知领域,人类认知宇宙才刚刚开始,怎能把艺术标准化呢?标准定早了艺术怎么发展呢?人类和艺术是共存亡的,人类认知才刚刚起步,如果把艺术规范化,艺术还能怎么发展呢?我们现在的重彩艺术实际上是拓宽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空间。
兰:重彩艺术这个理念现在有没有人支持呢?
王:我只是对重彩艺术搭了个框架,当然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去完善。不同意此观点的人是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也是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独行侠。因此这个“四不像”的艺术形式是不能参加全国大展的,因为重彩艺术的标准和他们展览的标准不一样嘛!因为全国大展是分画种的,而重彩艺术是要打破画种界限的。
兰:模糊画种?
王:是的。有一次我在北京和一个中国画的理论家讨论,我的模糊画种边界论,使他陷入了理论盲区。理论家穷其一生力图将画种量化和细化,而重彩艺术是模糊画种论,这让许多教条主义者找不到北而失语。重彩艺术才刚刚开始还有待完善,但是前景我很乐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人是研究苹果的,另一个人是研究梨子的,两个人都是专家,突然嫁接出来了一个梨苹果,那么两位专家在面对新物种时就不是专家了。你不能说梨苹果是不存在的,但梨苹果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找一个合适的词语去界定它,既然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
我的生宣画重彩写实“佛”的系列,在国内巡展时遇到不少理论家,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画得非常好,在生宣上画重彩超写实,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非常了不起,但是在从古至今的中国画理论里是找不到理论支持的。也就是说我的艺术实践先行了,理论滞后了。我说既然是这样,你们理论家可以把我作为一个选题研究嘛。他们说我的作品受众很小,校方不可能拨科研经费,他们要研究大众接受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努力改变重彩艺术理念受众群,使小众变大众。
兰:您在生宣上画重彩写实“佛”,说是要达到油画或者工笔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油画或者熟宣上做出来,您为什么还要在生宣上画呢?
王:您说的布本油画和熟宣纸工笔画,和在生宣上画重彩写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生宣重彩写实是让人们对中国画材料负载的一个全新再认识,同时也挑战了画家对传统材料的驾驭能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兰:您在生宣上画和工笔熟宣上画有没有区别?
王:区别和差异都是很大的,如果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效果就会一目了然。
兰:这个差异体现在哪里?
王:我画的这个重彩写实是熟宣纸上工笔达不到的,油画也达不到的。因为我用的是国画的颜料和宣纸,它是哑光的(这个是和油画的区别);生宣纸是可以正反两面画的,从反面画后浸染到正面的这种效果是熟宣和油画完全表现不出的效果。我在生宣上画的重彩写实作品和其它画种一比较就会有显而易见的差别,是把生宣纸的不可能变为可能。生宣重彩超写实,重要的是驾驭材料的能力。
兰:我明白了,同样是超写实,但在生宣和熟宣上画的话,呈现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王:是的,这个方法是我独创的。这个系列是我十几年前画的,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说画得好,就是没有理论家介入进来研究。其实人类有个惯性思维,见得多的东西就认可,没有接触过的或者没有记载的,一般都会反对。
兰:我有个问题,您现在自己已经做到的,这就是依据,干嘛还要理论依据呢?
王:这就是刚刚说的实践先行理论滞后。任何实践最后都要得到理论支持嘛。
兰:您把创作的过程、材料、方法一总结,不就是您的绘画理论了吗?
王:这样总结只能是在技巧层面的个人总结体会,理论界认可是我需要的。我没有透露我的绘画技法,是不想让社会上自己的假画遍地。目前没有理论家关注,造成人们总认为我的画是照片,展出时观众会拿手摸一下。其实这也是中国绘画理论界的问题。中国画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大家都不满意的,其实就是理论到实践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199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中国画误区》,就是对程式化和概念化的传统中国画理论的批判。
兰:还有一个问题是,之前和武汉工笔名家也谈到,就是重彩能画出“薄”彩的效果,那才是高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您如果看到我的原作就知道了。传统的中国画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画面没有冲击力和杀伤力,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嘛。
兰:您的意思是重彩艺术可以画出薄彩的效果。
王:纸本重彩是“以薄”为上,重复上颜色,这和传统的工笔画有相似之处,工笔画讲究的是三矾九染,但是我的重彩艺术也可以画到无限量次数,不是遍数多就好,只要画面的效果达到了就可以了。
兰:最终还是要看画面的效果。
王:是的,画面的效果不在乎作品画了多少遍,但是我们重彩艺术是提倡重复施色彩。
兰:三矾九染无非就是一个代数。
王:艺术是不择手段的,重要的不是手段,而是艺术效果。
兰:我的理解是:您的重彩也能达到薄彩的效果。
王:对。画面并不是要追求画了多少遍,那个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画面的效果才是硬道理。
兰:之前以为您在生宣上画重彩达到超写实的效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个效果油画和工笔画都可以达到。但是您现在讲了,这种在生宣上画出来的画面效果是和熟宣上不一样的,也和油画的效果不一样。
王:除了写实重彩,我还涉足了中国画领域里的写意重彩、重彩山水、重彩人物、重彩花鸟,觉得重彩艺术在中国画坛中完全可以占据制高点,完全可以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世界比赛。
兰:您刚刚提到了在生宣上做超写实没有理论根据,理论家也不愿意来研究,那我们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就可以形成理论了。但是您又不愿意把自己的技法透露出来。
王:其实我已经透露出来了,刚刚说了就是在生宣纸上正反两面画,但也不能再具体了。我需要的不是技法总结,而是重彩艺术发展可能性的理论支持。
兰:我觉得您可以把自己创作的过程都呈现出来,包括带学生,这样可以把重彩艺术发扬光大。如果您是担心一些人作假,我认为这是多余的。
王: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我探索的路后继有人。
兰:那些绘画大师是不是都会在技法上有所保留呢?
王:肯定是的,如果没有保留的话绘画界会模仿成风,千人一面了。
兰:技法是形而下的东西。有人说,大师的东西是不可以被复制的,能够被复制的东西都是比较简单的。
王:单纯的技术复制不难,但艺术指向和艺术内涵高度这种精神层面是无法复制的,超越不了的。
兰:我的意思是您不应该担心别人复制您的作品。
王:担心啊,复制不到位的话就会歪曲我的探索,学我者生,似我者亡!
兰:因为您的思想一直走在前面,有引领的作用的。
王:我只是按自己思路走,没有想这个事。
兰:因为我看到了您的作品后,觉得很有冲击力和感染力,或者您自己刚刚说的杀伤力。但是光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做还是不行的,还必须要让整个中国的艺术界,甚至是让世界的艺术界都知道这个东西,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呢?
王:有的,有一年在几个纸媒上做了一百八十多个页面的宣传,有点小效果。
兰:艺术理论界看到了您的作品后,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王:一句话:了不起。再深的就没有了。看来需要很长的时间沉淀。我的艺术走了一个冷门,大家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我的作品是一个多画种的混合体,如果认知不在一个层面,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结论也是截然不同。
兰:您的作品大家都看过了,也了解过了,大家还是沉默不语,我觉得是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在内心深处并没有认同您的艺术;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的艺术界主流和评论家们有可能还没有达到您的高度,您觉得怎样?
王: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标准和我的标准不一样,他们会停留在自己的认知区,若是走进我的思维世界就会形成对话。
兰:画法上或许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艺术的感染力这方面的标准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写文章一样,不管用什么样的叙述方法,只要文章能感动人都是好文章。
王:您说到本质了。
兰: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多个人偏见的。
王:是的,对于现在的展览有些人说他们不是按照艺术的标准,而是根据评委的好恶。
兰:这也是我刚刚想说的,可能是他们的认知还没有达到您艺术的高度。
王: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高度,只是另辟蹊径。
兰:对的。就像书法界的兰亭奖一样,刚一出来马上就有很多的质疑,其实一个人不在这个圈子里是很难获奖的。
王:对的,如果您特别在乎这个奖项的话它就特别重要,如果您不在乎的话,它就一点儿也不重要。全国的大展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为它而奋斗,特别在乎。我不在乎这些,就不去参展,就没有烦恼了。
兰:有些人对您的作品保持沉默,是他们的认知不够,因为他们不是从艺术的真正意义去考量一些东西,用不客气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平庸,您是走在艺术的前面的,思考的问题更远一些。
王:为什么我们的重彩艺术里多了一个当代意识呢?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画家不思考当下问题,现在很多人一开口就是传统,传统是什么呢?我原来就说过很刻薄的话,传统就不是东西!其实,传统是一个中性词,有好有坏,我们现在一提到传统好像就是一个褒义词,现在我们随便画的东西将来都是传统,所以历史上所有东西都是传统,但是我们一概把传统定义为褒义词的时候,这就错了。其实,传统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种文化精神。
兰:您刚刚特别强调我们的创作要有当代的意义和当代的思考,那么现在其他画家都没有当代的思考吗?
王:现在有很多人在思考,很多人没有思考。我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使命感逼得我一定要思考,虽然我不能左右别人的思考,但是我自己可以左右我自己。
兰:前面也说到了我们要有当下的思考,重彩艺术向未来发展的空间比较大,有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去探索,那么那些所谓的传统画家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吗?
王:我认为,相比而言重彩艺术发展空间要大些。重彩艺术多了几个元素肯定会跑得远些。我认为艺术的脉络就像是一个链条一环一环地扣在一起,承上启下,如果只能承上而不能启下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兰:这就是艺术家和画家的区别。
王:比如画家和书法家。现在存在一部分画家是在重复古人和前人的现象,但在书法界里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
兰:如果承上了就不能启下了吗?
王:有的能承上启下,有的就不能。不能承上启下就成不了艺术脉络上的这条主线。我认为张大千就是承上不能启下的画家,在我心目中他不是大师。他不能启下,只是一个优秀的书画家而已。因为大师一定是要承上启下,而且会影响几代人。
兰:这个观点我也有点赞同。您认为艺术界哪个是大师?
王:我欣赏林风眠,他是重彩的先驱,远远高于张大千。
兰:吴冠中呢?
王:我也欣赏吴冠中,更佩服他。他有高度,他把西方的东西融入到中国画中,改变了中国画里面的不足。艺术家不能在艺术辅道上跑,要上主道上跑。作为一个远观者,我发现现在书法界的问题比绘画界的还多一些。因为西方的艺术家眼睛是长在脑门上,眼光会看得更远一些,我们中国画家的眼睛是长在后脑勺上,一直盯着后面。因此,西方艺术家是否定前人而发展,我们是继承前人而发展。周韶华先生的思想对我的启发比较大,这个思想就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重彩艺术的宗旨。
兰: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得很有意思,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内容很多,最关键的是对我们的创作有些解读。因为之前这个专题发出来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和我聊,说不是很理解您的作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解读,让更多的读者理解您的创作理念,这个很有意义。
王:我和别的书画家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不按套路走。
兰: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观点还是很默契的,做事总是很老套也是没有意思,比如我们的访谈栏目就是要有新的观点出来,给读者呈现更多。
王:我为什么画了那么多的系列作品,就是一直在修正自己,担心自己跑偏。
兰:您的东西我们还是会持续关注,有新的想法的话都可以经常交流,这样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刚才我说了,不能只让部分人知道您,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慢慢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认为现在的学术界还有待提高,需要站在新的角度和高度来看待新生事物,以避免平庸。
王:我忌讳平庸这个词,因为我自己也很平庸。理论家在他们的领域有高度,我的新领域他们没有觉悟,是理论家的处女地。你们媒体有不同的发声,这样办媒体才有意义。
兰:我还有个想法,就是这个访谈做出来之后,我们再请几个画重彩的画家对您的观点座谈一次,一步一步往前推。
王:这样也可以。
兰:到时候把周韶华先生也可以邀请过来。
王: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有个个展,到时候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形式来做一下。您可以做我的学术主持。我去年的个展就做了个新模式:展览的开幕式、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合在一起,大家围绕重彩艺术来讲,然后再去看展览,这个形式还是比较新的。
兰:还是要以您的艺术为主,大家围绕您的作品来谈。
王:是的,如果有人想看展览就看展览,想参加座谈会就参加座谈会。
兰:您是很有想法的,期待您有更多的作品出来。
王:谢谢您关注重彩艺术,支持重彩艺术。(作者:兰干武/书法报副主编兼执行主编)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