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自古以来,名字叫“村”“庄”的村子,繁若星辰。
譬如,在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水浒传》里的“大头领”晁盖家住东溪村,宋江家住宋家庄,“三阮”住在石碣村,厮杀得昏天黑地的还有“三打祝家庄”等。
即使是书写历史大场面的《三国演义》,开场“桃园三结义”之刘皇叔刘玄德便是涿县楼桑村人,而张飞所说的“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此“庄”此“园”,正是刘、关、张结义之圣地也。
即使是谈神弄怪的《西游记》,也有猪八戒心心念念的高老庄,以及“异域风情”的车迟国元会县陈家庄,等等。
只有《红楼梦》是个“异数”。书中既不详写具体时间(年月),也不细写具体地点(村庄),就算是“村姥姥”刘姥姥的家乡,也只写生活在一起的女婿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去住了”。只是在写到贾政、贾宝玉父子等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方才提起“杏花村”,并题写“稻香村”——毕竟还是绕不过村庄去的。
文学是现实的投映。而现实中的“村”“庄”,更是多得指顾皆是,不可胜计也。
之所以想到“村”“庄”这个话题,是因为前几天我的山阴老乡、山西大学历史系张世满教授,带着他主编的《山阴杨庄学校记忆》一书,在京举办了一个小型赠书座谈会。我在会上简略谈了谈“微观史学”,顺带还解析了杨庄的“庄”字和杨庄第一大姓“剧”字。
没想到,座谈会视频在家乡几个微信群同步播放后,反响讨论得很热烈。一位在京工作多年的老乡,次日清晨即给我打电话,说你只解释了村庄的“庄”,为啥不把“村”也一并讲一讲呢?
讲,自然是谈不上的。不过,我对于“村”“庄”二字,确乎有一些历史资料的耙梳归纳,以及一点点不太成熟的看法。权当作野人献芹,聊博一粲吧。

《说村庄》
我的故乡在雁门关外的山阴县高庄村。
何为村?何为庄?村与庄是个啥关系?
先从“庄”说起。
在我童年的时候,看到村口道路两旁人家的古老院墙上,依稀留存着大大的两个字“髙莊”。
“髙”字很“髙”,在孩子们的眼中,浑如房顶或烽火台,爬上去是需要借助梯子的,所以我们童年时都会讲一个字谜:“一点一横长,梯子搭上房,大口张开嘴,小口往里藏。”谜底是“髙”字。村子里高、李、常是大姓,最初高为第一大姓,故名高庄。
“庄”是“莊”的简化字。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的统一,因而大多字可以“望文生义”。
其实,汉字最根本的特性是象形文字,“象形”者,先从“形象”到“意象”,再到“意思”和“意义”。故“望文生义”是“说文解字”的正途。
“莊”字最初指的是道路。
现代人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其实,我国古代的城市、宫院以及村庄,也是先从修建道路开始的。

我在家乡高庄村南,背后是馒头山与草垛山
解释道路的文字有些繁琐,不耐烦的读者可以跳过去——只在有关道路的“九达”解析中,瞄一眼“六达谓之庄(莊)”即可。
我国现存最早的工具书、“十三经”之一的《尔雅·释宫》,对道路的解释为:
“一达谓之道路”——“达”指通达,也指路口,笔直的一条路叫做“道”。故“道”亦引申为“人间正道”之“道”,也就是“道德”的“道”。东汉刘熙《释名·释道》:“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这是“道路”的基本义。
“二达谓之岐旁”——一条路边又踩出一条小路,叫做“岐旁”。东汉许慎《说文》:“跂,足多指也。”“岐”乃“跂”之假借。而《释名·释道》对“岐旁”的解释是:“物两为岐,在边曰旁。”“岐途”(歧途)与“旁道”,歧路多亡羊。
“三达谓之剧旁”——“剧”是“劇”的简化字,“劇,甚也”,指道路交错。《说文》讲:“劇,務也,从力,豦声。”《释名·释道》亦讲:“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恒见修治,此道旁转多,用功稍劇也。”“古者列树以表道”,指道路两旁栽树,起到路标指引的作用,现在不少村庄里的道路还是这样的。“旁转多”指拐弯路,修建的时候用工费时较多。东晋学者郭璞为“劇旁”作注:“今南阳冠军乐乡,数道交错,俗呼之为‘五劇乡’。”
“四达谓之衢”——十字交叉有四条路口的道路,叫做“衢”。《释名·释道》:“齐鲁间谓四齿杷为欔。欔杷地则有四处,此道似之也。”郭璞对“衢”注曰:“衢,交道四出也。”指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清史稿》称武汉为“九省通衢”,《清实录》亦称正定为“九省通衢”。
“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五条路口的道路叫“康”,《释名·释道》曰“康,昌也;昌盛也。车步并列并用之,言充盛也”。六条路口的道路叫“庄”(莊),《释名·释道》曰“莊,裝也,裝其上使高也”。“康”与“庄”通称为“康庄大道”,喻指道路出口多且平坦广阔。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康庄之衢”之语,明代王阳明《传习录·答聂文蔚》有“康庄大道”之说。
剩下的三句,也一并说说吧。
“七达谓之剧骖”——七条路口的道路叫“剧骖”,郭璞注:“三道交复,有一岐出者。今北海(郡名,今山东潍坊)剧县有此道。”“剧”(劇)字再次出现,那就多说两句。我觉得,“劇”字也可以这么解读——“劇”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豦”,读劇,也读去。《说文》:“豦,斗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虍之斗,不解也。司马相如说:豦,封豕之属。一曰虎两足举。”“丮”“虍”“豕”分别解析一下。“丮”读作自己的己,《说文》:“丮,持也。象手有所据也。”“丮”象形手里拿了个打斗的家伙。“虍”读作胡,《说文》:“虍,虎文也。象形。”“虍”是虎皮的花纹,这里也代指老虎。“豦”字篆书,好像老虎站起来的样子(即“虎两足举”)。“豕”指野猪,所谓“封豕长蛇”,“封豕”指大野猪。“豦,斗相丮不解也”,形容老虎和野猪大打出手,纠缠一体,打斗得难分难解。“骖”字容易理解,读作参加的参,《说文》讲:“骖,驾三马也。从马,参声。”《释名·释道》又说:“骖马有四耳,今此道有七,比于剧也。”综合起来,“剧骖”指道路交错,路口甚多(七个),但是路面很宽阔,可以通行三匹马并驾齐驱的车辆。
“八达谓之崇期”——八条路口的道路叫“崇期”,亦即“四道交复”者。《释名·释道》:“崇,充也。道所多通,人充满其上,如共期也。”《说文》:“崇,嵬高也。”其他古代字书和学者们亦讲:“崇者”,“高也”,“大也”,“尊也”,“聚也”,“多也”,等等;《说文》还讲:“期,会也。”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进一步解释道:“期,日行迟,月行疾,似与日期会也。”故“崇期”形容道路纵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频频交会。
“九达谓之逵”——九条路口的道路叫“逵”。《释名·释道》:“齐鲁谓道多为逵师,此形然也。”“逵”字也写作“馗”——“望文生义”即知为“九条道”。《说文》:“馗,九达道也,似龟背,故谓之馗,从九首。或作逵,从辵坴。”“逵”为“九达道也”,关键在于它是什么样的“道”?愚窃以为,“逵”为“云路”,或曰“天路”。《易经·渐卦》从“初六”到“上九”六个爻,分别为“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陆”——“鸿”是大雁,从“干”“磐”“陆”“木”“陵”“陆”,逐渐从低处走向高处,或曰飞向高处。三爻的“鸿渐于陆”,与六爻的“鸿渐于陆”,不应该是同一个“陆”。三爻“鸿渐于陆”的“陆”是陆地,六爻“鸿渐于陆”的“陆”应当是“逵”。“陆”的繁体字是“陸”,与“逵”相似,可以假借。清代大儒刘沅曰:“陸,当作逵。逵,云路。”另一位清代经学家惠士奇亦云:“陸,天衢也。”大雁从“干”“磐”“陆”“木”“陵”“陆”,逐渐从低处向高处一路走来,最后是要起飞的。诚如《诗经·豳风·九罭》之“鸿飞遵陆”,这个“陆”也是“逵”,就是鸿雁飞过的“天衢”“云路”。古代读书人的抱负胸襟多是“云路鹏程九万里,学窗萤火二十年”,历尽艰辛成大道,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故“九达谓之逵”,特有想象力,超赞!
三纸无驴只说“道”。且回到“莊”字上来。
有人生活的地方,必有道路通行。“莊”是从道路开始的。
东汉许慎《说文》:“莊,上讳也。”因为东汉的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叫刘莊,故讳其名也。前面讲过,与许慎同时期稍早一点的刘熙《释名》解“莊”,仍然沿袭《尔雅》“六达谓之庄(莊)”——“莊,裝也,裝其上使高也”。后来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讲:“莊,草盛兒。”“兒”,即貌也。直到北宋陈彭年、丘雍《广韵》才讲:“莊,田莊。”
所以,从“庄”(莊)字历史演变来看,最初指道路,后来形容百草丰茂,再后来才指田庄、村庄。
“庄”字的繁体“莊”——上面“草字头”,左边是一片树叶两片树叶的“片”翻过来——“爿”,右边是战士的“士”。
重点说“爿”。“爿”读作墙,是一劈两开的木头之左边那一半,“剖木为二,左半为爿”。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本家叔叔李阳冰做过县令,也是个书法家。李阳冰讲篆体“木”字:“木字,右旁为片,左半为爿,音牆”。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文》中的“牀”字时亦讲:“《九经字样》‘鼎’字注云:‘下象析木以炊。篆文木,析之两向,左为爿,音牆;右为片。’”“鼎”是《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之一的“鼎卦”,可见是个很古老的字。
“火风鼎卦”的“鼎”,是古代煮食物的青铜器,象征帝业王位,要不为啥说“问鼎中原”呢?《说文》:“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易》卦:巽木为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鼎”字的上半部分,乃盛食物的器具;下半部分,是一块木头劈成两半的柴火,左为“爿”,右为“片”。“爿”字也读盘,指劈开的木片和竹片等,引申为量词。如一片一片的田地、树林,以及用木棍、竹片或庄稼秸秆围起来的地片,就像北方农村早年围起来的院子,或者种植蔬菜的小菜园子。现在的店铺也说“爿”,如一爿小店,一爿酒店,一爿书店等。
还有“士”。《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古代学者还有各种解释,诸如:“士者,男人之通称”,“士,事也,谓能治其事也”,等等。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所讲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仕”(《论语·子张》),也是做事的意思。《说文》:“仕,学也。从人,从事。”其他学者亦讲,“仕,事也”,“仕与事通”,“从王命为仕”,等等。“从王命为仕”就是做官,做官就是做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故先从“干事”做起。
综上所述,“莊”字由三部分构成:上有“草字头”,指植被植物,包括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等,乃人类生存生活的必备条件;下面左边为“爿”,有田地、菜园,以及用木板、木棍或竹片围起来供人居住的院子;右边为“士”,“推十合一为士”(指人士众多),也就是一群能做事情的男子。
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当然,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不就成其为“莊”了吗?这个“莊”字,活像一幅生动的生活画卷,颇有人气与烟火气。
至于“莊”字后来为什么改头换面变成了“庄”,是由于古代也有人把“莊”写成“㽵”的。譬如,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即有:“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㽵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唐人孙愐所著声韵学《唐韵》即收入“㽵”字。还有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明代文学家杨慎,亦留下“海㽵岑寂地,车辙满荆扉”之诗句。尽管“㽵”字很个别,但毕竟有人使用,便成为“莊”的异体字。所以1956年颁布《汉字简化方案》,文字专家们就把“莊”字参照“㽵”,进一步简化为“庄”了。
“庄”字“广土”而缺“士”,人都到哪里去啦?
再说说“村”吧。
这个说得简约点。
我读古籍——特别是“经书”,与国家、城市和村庄相关联的字,一般遇到“邑”字最多。譬如,《易经》里的《比》有“邑人不诫”,《泰》有“自邑告命”,《晋》有“维用伐邑”,《井》有“改邑不改井”,《谦》有“征邑国”,《升》有“升虚邑”等;《尚书·洛诰》有“作周大邑”,《召诰》亦有“乃社于新邑”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商颂·殷武》亦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等等。《尔雅·释地》解释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宋儒邢昺疏:“坰为边畔,去国最远。”你看,有“邑”有“郊”,有“牧”有“野”,有“林”有“坰”,就是没有“村”。
“村”的本字写作“邨”。
凡有“耳朵”偏旁的字,“左耳为阜”,“右耳为邑”,“阜”与“邑”均与国家、城市、村落以及地形地势有关。《尔雅·释地》讲:“大陆曰阜。”《说文》亦讲:“邑,国也。”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注:“邑之名,古大而今小。”也就是说,上古的“邑”多指诸侯国,后来的“邑”也泛指民人聚居之城市与村落。东汉刘熙《释名·释地》讲:“四井为邑。邑,犹俋也,邑人聚会之称也。”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亦阐释道:“邑为通名,大不过千室,小不过十家。”
这说的不就是城镇与村落吗?
汉代以前,见“邨”而不见“村”。譬如,东汉许慎《说文》讲:“邨,地名。从邑,屯声。”宋代大儒徐铉注:“今俗作村,非是。”
东晋之后,“村”字才出现,之后“邨”“村”并用之。现存古典文献中,“村”字最早见于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而《晋书·李特载记》则写作“邨”:“可告诸邨,密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
再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病中得樊大书》诗:“荒邨破屋经年卧,寂绝无人问病身。”宋代诗人梅尧臣《颖水费公渡观饮牛人》诗:“渡口饮牛归,邨墟夕阳里。”金代诗人元好问《跋酒门限邵和卿醉归图》诗:“太平邨落自由身,童稚扶携意更真。”
还如,同样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咏怀》诗:“如何办得归山计,两亩村田一亩宫。”唐代诗人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宋代诗人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诗:“昼出耘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唐宋金五大诗人,“荒邨”“邨墟”“邨落”,“村田”“村野”“村庄”,各自挥写,不尽相同。
其他各种字书辞书,也是晋代以后才收入了“村”字。譬如,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村,聚坊也。”唐代慧林法师《慧琳音义》:“人众所居曰村。”北宋陈彭年、丘雍《广韵》:“村,墅也。”北宋丁度《集韵》:“村,聚也。”大同小异,不一而足。
现在看来,“村”与“庄”的区别在于,省、市、县、乡、村,“村”是一级基层行政单位。这也是古已有之。据《旧唐书·官职志》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又据宋元时期史学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项安世《家说》曰:‘古无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为村,置村正一人,则村之为义明矣。’”
所谓“置村正一人”,就是任命村长一名。
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了“村正”,亦即村长。
至于“村”字是怎么造出来的,我觉得与村子里栽种生长着各种茂盛的花草树木大有关联,大致与《尔雅·释地》所说的“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相仿佛。故仿照《说文》之体式试释之:“村者,林也,树木花草簇拥之地也。从木,寸声。”
难道不是吗?
只要比照一下,唐代诗人李商隐《夜冷》诗句“树绕池宽月影多,村砧坞笛隔风萝”,以及宋代诗人陆游《游山西村》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知道“村”字与花草树木以及环绕村庄的大片庄稼、优美生态密切相关也。
而且,还不止于此。
“村”字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村者,材也,盛产材也。小材,大材,实用之材也,栋梁之材也。”昔者,工农商学兵之主力军源源不断来自农村;而今,生产生育之生力军仍生生不息来自于农村。一家没有人,便不成其为家;一村没有人,便不成其为村;一国没有人,便不成其为国。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意识到孟夫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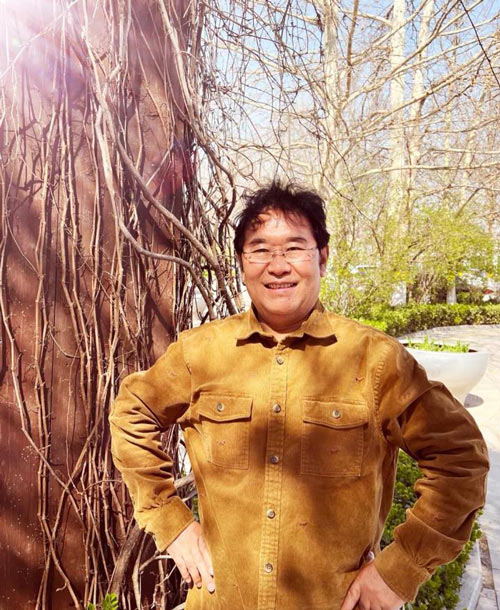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